颠覆|未来已来·互联网颠覆性技术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综述)
时间:2024-06-28来源:黑鸟智库微信公众号点击量:356
2024年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历次产业革命都是由颠覆性技术推动的科技革命促成的。人类文明历经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特别是科技革命,都从颠覆性技术中萌发,从金属冶炼技术、火药制作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原子能源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到网络信息技术等,每一项新技术都颠覆生产生活,带来时代变迁。其中,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新技术,赋能人类创造出数千年农业社会、数百年工业社会都未曾创造的巨大财富,并主导当下世界文明中心的变迁。当今世界正历经百年变局,颠覆性新技术的创新不断突破地域、组织和技术界限,发出强劲跨界创新势能,重塑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变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我们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必须看到,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新技术进入高速发展期,从技术到应用迎来新一轮重大突破,呈现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快速扩散的总体态势,正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颠覆性新技术不断推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浪潮,推进对现有互联网进行大重构大设计,推动智能泛在、虚实共生的数字世界全面展现开来,人类社会迎来第五次颠覆性革命浪潮。从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数字人、元宇宙到Web3,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卫星互联网到量子信息,它们既是助推现代经济社会变革的强大引擎,也是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颠覆性这个概念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颠覆性创新,既有秩序过程被打断打乱之意,也有结构上混乱、错乱和剧变之意。颠覆性创新不是渐进式创新,而是打破经济周期的创新,重构各个行业,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颠覆性技术概念则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与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颠覆性技术:赶上浪潮》中首次提出。1997年,克里斯坦森又撰写专著《创新者的窘境》指出,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它能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
颠覆性技术与人们常说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等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颠覆性技术强调技术的颠覆性和变革性,前沿技术强调技术的前瞻性和先导性,新兴技术强调技术的新颖性和尖端性。一项前沿技术或新兴技术能否成为颠覆性技术,主要是看其是否会产生颠覆性技术和社会效果。例如,人工智能自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就被首次提出,经过60多年发展才进入21世纪三大尖端技术(纳米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行列,被公认为改变未来的颠覆性技术。一般来说,颠覆性技术具有四个特质:技术的先进性,即具有超越性和替代性,打破原有技术体系,实现对传统或主流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作为新兴替代性技术形成新的技术轨道和生命周期;技术的变革性,即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改变现有技术的作用机理,破坏原有技术发展路径,使先发国家以技术突袭方式形成与后发国家的技术代差,同时破坏现有技术发展模式,在多个领域提升各种能力,影响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促进经济社会变革;技术的风险性,即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内部技术和外部场景的复杂性,技术发展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各环节的交互关系又放大彼此的风险影响,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一方面新技术挑战或彻底取代已有技术,突破和穿透原有监管边界和监管手段,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存在风险性;技术的非均衡性,即具有渐进性和不平衡性,技术发展演变需要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在某一时间点出现质变点后才会显现颠覆性影响和效果,同时受外部条件和技术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在不同国家和行业发展不平衡。彼得·科威(Peter Cowhey)和乔纳森·阿伦森(Jonathan Aronson)合著的《数字DNA:全球治理面临的颠覆与挑战》一书,探讨了通信技术产生的颠覆性变革如何改变国家创新体系。目前,颠覆性新技术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不仅带来重大产业创新变革,也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科技的变革带来权力的转移。纵观世界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变革,颠覆性新技术变革始终是一个关键变量。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发展基本贯穿“科技强→经济强→国家强”的路径。如今,全球正在加速进入科技革命跃迁、经济范式转换和生产要素重置的重要变革期,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出现集体跃升和重大变革。颠覆性新技术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为人类带来巨大便利和社会福祉。同时应看到,新一轮颠覆性新技术创新呈现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把人类带到一个“VUCA”(易变性、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1]时代,许多固有的定式、惯性和运行系统受到冲击,事物认知维度遭到挑战,事情变得越发复杂,相互关联和影响加剧变化。“VUCA”一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军方术语,指的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边世界,用以描述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新一轮颠覆性新技术正在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例如,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系统和人类能力的颠覆,脑机接口对人机关系及人的主体性的颠覆,虚拟现实、数字人、元宇宙对人类活动空间和拟人化生存的颠覆,云计算、大数据、量子信息对人类计算和存储资源利用和组织方式的颠覆,物联网、数字孪生对地理空间和万物数字化改造的颠覆,区块链对社会底层组织逻辑和社会互动关系等的颠覆。这些新技术正如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力量,不仅会改变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也会改变政府、社会、企业、个人间的权力分配。新一轮颠覆性新技术正与产业变革蓬勃推进,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重构国家力量对比,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世界地缘格局,颠覆国际权力分配。能否抓住这一轮颠覆性新技术变革蕴含的重大机遇,有效规避可能的风险挑战,成为大国竞争决胜的重要砝码。
必须看到,新技术是发展利器,也会成为风险源头。新一轮颠覆性新技术发展具有不稳定性,运用不当、管理不好会引发重大风险。“技术既不好也不坏,它也不中立的。”1985年,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技术史学教授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基于冷战时期案例总结提出科技六条定律,其中第一条就是“技术既不好也不坏,它也不是中立的”。他用定律来诠释和警示技术的力量与普及所引发的不安。自16 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议题。信息技术变革就像一柄新式双刃剑,在提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愈发难以预知与控制。各国认识到,全球流动的信息和数据,需要进行有效管制,秩序和自由在全球网络治理中应均衡考虑和体现。例如,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基因编辑、转基因、器官移植等新技术发展应用,将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难题。而现有法律法规总体滞后于新技术发展步伐,不同国家间法律各异,空白地带和漏洞很多,难以及时有效管控新技术领域。
新一轮颠覆性新技术通过与社会经济生活广泛链接,正嵌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逐渐展现出巨大影响力。新技术通过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改变着这些领域运行的底层逻辑,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等构成挑战。新技术安全也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信息技术攻势将进一步规模化、智能化,不断推升信息技术领域攻防的强度、频率、规模和影响。例如,美西方国家对“深度伪造”“计算宣传”等人工智能的应用,给其他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带来挑战。美国大力发展基于卫星的通信网络,可穿越太空天空、跨越边境国界,再加上其掌控互联网根服务器,一旦采取停服、断网等极端化手段,部分主权国家将丧失对本国地域、空域互联网的控制权;暗网、区块链等借助加密通信等手段,可以隐藏违法不良信息和网络攻击人员身份。斯诺登事件、伊朗“震网”事件等表明,美国正借助其互联网控制地位威胁他国关键领域安全。同时,信息通信技术开始深度介入选举、公投等政治领域,脸谱、谷歌、推特等技术巨头,都被曝深度介入政治过程。剑桥分析公司及其母公司采用大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舆论操控,曾影响60多个国家260多场选举。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以及智利、阿根廷、西班牙、哈萨克斯坦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现抗议运动,“社会抗议+社交平台”成为鲜明特点,各国政府传统应对方式基本失效。美已升级网络空间司令部,网络空间正式与海、陆、空和太空并列成为第五战场,网络空间军事化进一步加剧。
总而言之,人们对颠覆性信息通信技术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恨是因为它也具有破坏性,已有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新改造,人们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或多或少会影响既有状态。例如,新技术变革会冲击各国现有经济社会格局,带来技术垄断、数据霸权、技术性失业等新问题;新技术会突破传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边界,突破传统的行业准入和管理界限。对于颠覆性信息通信技术,用的好是机遇,管不好就是挑战。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曾几次错失科技革命契机。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不断积聚。5G技术处于世界领跑位置,云计算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中国也已成为世界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数据中心之一。同时必须看到,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并未有效转化为全球科技能力,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信息技术和应用交叉研究迟滞。如何把我国积累的信息通信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科技优势,促进技术和应用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综合全球科技变革经验,新一轮颠覆性技术变革带来广泛深刻的变化,技术革新蕴含着巨大的技术红利和发展契机。现在,美西方国家已将颠覆性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最具变革性的科技突破方向,雄心勃勃地制定和推进发展战略。同时,新技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也产生一系列颠覆性重大影响,驱动经济业态、社会治理以及权力运行方式的创新转型,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未来已来,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相比,新一轮信息通信技术变革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颠覆性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浪潮,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既积极把握新技术变革提供的历史契机与发展动能,又有效克服颠覆性技术涌现带来的破坏冲击与风险考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1] VUCA代表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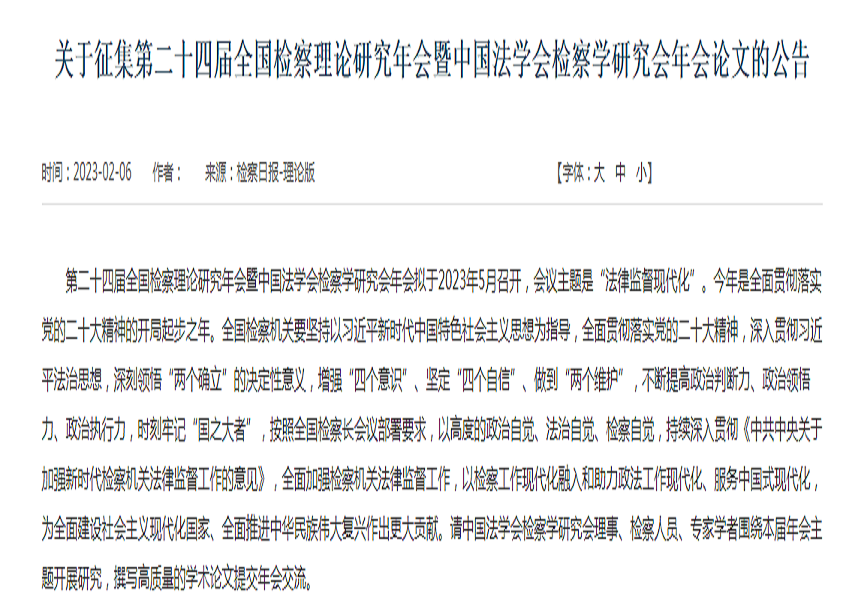
关于征集第二十四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论文的公告
第二十四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拟于2023年5月召开,会议主题是“法律监督现代化”。
2023-02-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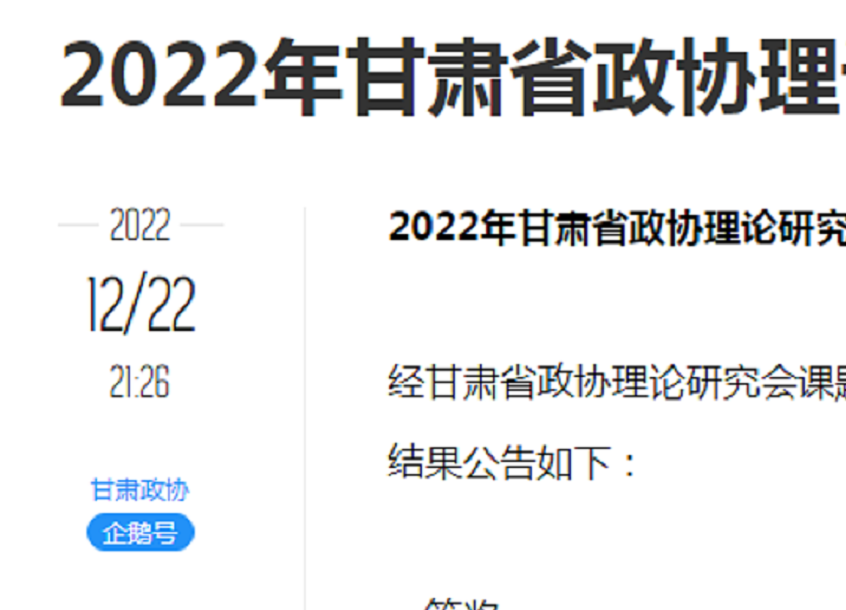
2022年甘肃省政协理论研究会课题结项公告
经甘肃省政协理论研究会课题专家组评审,2022年立项的10项研究课题获准结项,现将评审结果公告如下
2023-01-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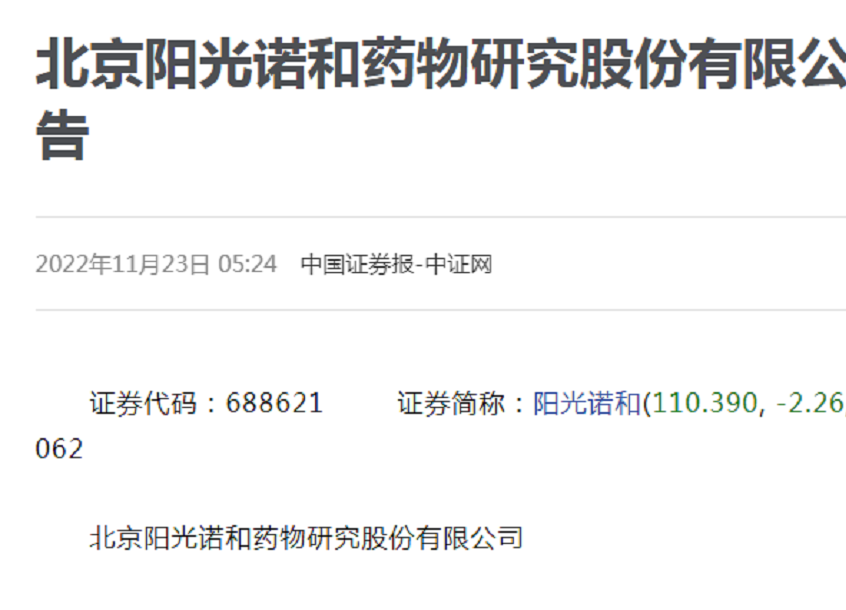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12-20
-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学术论坛公告
为了促进我国语言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汇聚学科交叉资源,推动我国语言服务学科建设,培养高质量的语言服务人才,并对当前语言服务领域中的热点和问题深入研讨,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拟于2022年11月19日承办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真诚欢迎语言服务界的广大学者和同行参会,期待与广大语言服务界同仁就新时代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热烈讨论。
2022-12-08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0374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03744号


